- 用心翻譯每一天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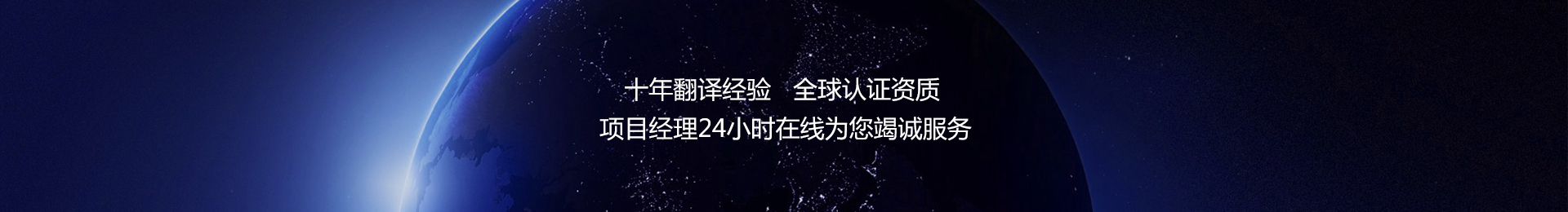
聯(lián)系我們
全國統(tǒng)一服務(wù)熱線:
電話:021-58446796
公司QQ:732319580
郵箱:daisy.xu@easytranslation.com.cn
網(wǎng)址:www.jpgfs2012.com
地址:上海浦東金橋開發(fā)區(qū)金豫路700號6號樓1樓
作為一家法律翻譯公司,我們在翻譯合同文件的過程中,深知每一個詞,每一句話在界定合同雙方義務(wù)和責(zé)任方面的重要性。所有的法律翻譯譯員都以“差之毫厘,謬以千里”的古訓(xùn)來警示自己。在翻譯過程中,為確保術(shù)語的專業(yè)性和準(zhǔn)確性,我們的譯員和校對人員會使用各類法律專業(yè)詞典,其中在完成英譯漢翻譯任務(wù)時,我們使用較多的就是《元照英美法詞典》。《元照英美法詞典》是我國第一本全面介紹英美法基本制度方面的詞典,它在概念上填補(bǔ)了我國法律界在這一領(lǐng)域的空白。這本詞典的編撰耗時數(shù)十年,凝聚了大量法律專業(yè)人士的心血。《元照英美法詞典》的背后是一群默默無聞、埋首工作的法律研究人員,其中既有代表人物薛波,也有眾多垂垂老矣但仍然秉承學(xué)術(shù)精神的法律專家。這本詞典中的每一個詞典和每一個釋義都凝結(jié)了他們的心血并體現(xiàn)了他們一絲不茍的治學(xué)精神。作為翻譯工作者,這些詞典編撰及翻譯人員為我們樹立了 一個良好的榜樣,并親自用自己的行動告訴我們,什么是嚴(yán)謹(jǐn)治學(xué)態(tài)度。正是這群熱愛法律并胸懷理想的法律人士的堅(jiān)持,我們才有幸在今天獲得如此有份量的專業(yè)法律詞典。以下文章摘自:唐律疏議:“薛波和他的《元照英美法詞典》 (一)“對法律的初學(xué)者,我頭一條建議,向來是請他們買一部好的詞典,并且請教它。”—— 哈佛大學(xué)前法學(xué)院院長羅斯科·龐德 1993年,29歲的薛波還在中國政法大學(xué)讀研究生,風(fēng)華正茂,躊躇滿志。然而他在學(xué)習(xí)法律的過程中并不那么順利,閱讀外文書時,書店、圖書館都找不到好用的法律英語工具書,勉強(qiáng)用一本,由于都只是簡單的對譯詞形式,而沒有其法律涵義的詳釋,總是覺得詞不達(dá)意,不得要領(lǐng)。甚至于,有時還會遇到一些現(xiàn)在看來很是荒謬的錯譯。一個極端的例子是“Asylum”,這個意為政治庇護(hù)權(quán)的世界通用的法律術(shù)語,我國1954年憲法中將其錯譯成居留權(quán),一錯30年,途經(jīng)1975年、78年、82年三次修憲未有察覺,直到1985年修憲時才終得以糾正。年輕的薛波意識到了缺失基本法律英語工具書暗含著的風(fēng)險,我們說“失之毫厘,謬之千里”,用基本詞匯、基本概念為基筑造起來的制度大廈,會不會終有一天因地基里隱藏著的無數(shù)蟻穴而轟然倒塌?! 《英漢法律詞典》的發(fā)愿便在這樣的環(huán)境和思考中萌生了。薛波與時任司法部教材編輯部副主編,并同樣對法律英語工具書的缺失充滿了擔(dān)憂的閆欣達(dá)成了合作,隨后及成立英漢法律詞典編纂工作室,一切工作順次展開。1995年與外文出版社簽訂合同,由于對困難嚴(yán)重估計(jì)不足,薛波很是“勇敢”地約定:一年之后完成交稿! 93年至95年間,薛波同時還與外文社合作編寫了《漢英法律詞典》,該詞典于95年出版。薛波“一年交稿”的樂觀估計(jì),就是奠定在這個基礎(chǔ)上的:既然已經(jīng)有了一個“漢英”,那么把“漢英”顛倒過來,不就是“英漢”了嗎?然而,隨著工作的一步步深入,出乎意料的困難竟將真正的出版日期延長至了十年后的2003年5月。“漢英”的工作是立足于中國法律制度,把中國本身的法律條文斷成術(shù)語,再翻譯成英文法律詞匯,只需做簡單的詞條搜集和編譯工作。但英漢詞典的制作,卻需以國外法律為基準(zhǔn),撇開對英語系國家的法律完全陌生不說,所搜集的英文材料反映的內(nèi)容也是千差萬別,同樣是英語文獻(xiàn),卻有來自美國的、英國本土的、馬來西亞的、印度的、甚至非洲國家的,致使同一個詞匯在不同的語境下表達(dá)的意思全然不同,換一個語境又總會看到其他語境下看不到的詞匯。90年代初期,我國對英美法尚還知之甚少,薛波自然也難以知曉“大陸法系”和“英美法系”的劃分,更無從知道在西方國家哪些資料才具有代表性和權(quán)威性。最初他們以沒有經(jīng)過很多甄別的五本國外出版的英文詞典作為藍(lán)本,把每個字母系的單詞分門別類、復(fù)印之后重新裝訂,在編譯每個詞目的時候都要對照五個詞典中的表述綜合整理。在整理過程中發(fā)現(xiàn)每本之間出入都較大,于是又往外拓展參考文獻(xiàn)。直至閱讀了大量文獻(xiàn),購買的書籍資料累計(jì)已達(dá)數(shù)十萬元之后,他們才開始意識到原來法律英語有著“英美法系”和“大陸法系”兩種不同背景下的不同表達(dá),并且更主要的還是反映了英美法系的內(nèi)容。運(yùn)作至此,時間就已經(jīng)過去三年。 當(dāng)薛波斟酌詞典是否也應(yīng)當(dāng)以表達(dá)法系為根本之時,他注意到日本在二十世紀(jì)三十年代就開始編纂、并經(jīng)數(shù)次修訂的《英米法詞典》,其中搜集的就是純粹的英美法術(shù)語。這一發(fā)現(xiàn)使他更篤定了自己的想法:所有的思維和行動都應(yīng)定格在這,用英漢的方式表達(dá)英美法的內(nèi)容。詞典的名稱也最終確定——“英美法詞典”,英文名為“English-Chinese Dictionary Of Anglo-American Law”。 (二) “這是個很奇怪的事,一部具有國家權(quán)威的詞典,卻由一群無職無權(quán)無錢的學(xué)人和老人編撰,他們做了我們整個司法行政教育系統(tǒng)想做而做不了的事。”——國家司法部一位司長 重新定位后,最初的一批稿子幾乎全部推翻,割棄掉其中相當(dāng)一部分不屬于英美法內(nèi)容的詞條,重新整理,重新起步。薛波與外文出版社的合同不得已一次次延期,關(guān)于詞典的花費(fèi)也難以遏制地增長。經(jīng)費(fèi)緊缺,工作陷入窘境,月末常常都是電話被停機(jī)之后四處籌一點(diǎn)錢再重新開機(jī)。薛波、閆欣不得不嘗試各種方式尋找援助。他們走訪了幾乎所有當(dāng)時較為著名的企業(yè)、律所、科研機(jī)構(gòu),找過拍賣公司爭取拍賣冠名權(quán),去涵英國大使館、澳大利亞大使館、國外基金會,甚至還專門給當(dāng)時的美國總統(tǒng)克林頓寫信尋求支持。為了節(jié)省郵資,寄往國外的信件都要由朋友帶出國后再寄。除了在工作室做編譯,薛波的工作就是騎著一輛自行車在外奔波,下雨天就把濕了的鞋放進(jìn)包里,看到路邊不斷閃過的商標(biāo)、廣告,他總會習(xí)慣性地聯(lián)想到:那會不會就是可以去尋找的希望? 然而社會對這部詞典表現(xiàn)出了冷漠,幾乎所有的努力都如石沉大海,沒有回音。最后《北京青年報》攥文為他們謀得捐款20多萬元,美國福特等基金會捐款100萬元,外文出版社預(yù)付稿費(fèi)40余萬元。至詞典出版之前,薛波以個人名義在外的借款已達(dá)40多萬元。 經(jīng)濟(jì)的拮據(jù)并沒有使薛波有所退縮,社會的冷漠也并沒有使他灰心喪志。薛波抖起精神與不斷涌現(xiàn)的困難打起了“持久戰(zhàn)”。英漢法律詞典編纂工作室”此時已更名為“英美法詞典編纂工作室”,這間不足10平米的小房間位于政法大學(xué)研究生院里的3號樓,如今該樓已經(jīng)變更為女生宿舍,這一間獨(dú)特的陋室在其中儼然是獨(dú)具風(fēng)景。推門而入,四壁圖書,中立書架,書架下緊靠書桌,留下兩條過道雖只能容納一人穿梭,卻能伸至屋內(nèi)每一位置。至于壁架、書架可利用之處也統(tǒng)統(tǒng)都不令其閑置,釘一個釘子就能掛目錄、備忘錄,貼一張條還能指路,這些條的功能就如同大辦公樓里的門牌,只不過辦公樓里分出的部門,在這里都壓縮進(jìn)了這10平米之內(nèi)。把剩下的空間填滿,最多還能容納10個人同時工作。置身其中,一眼就能看出,能把空間利用得如此充分,顯然不在一朝一夕的功夫。 薛波的背后,還有一個雖名不見經(jīng)傳,卻十分強(qiáng)有力的團(tuán)隊(duì)。工作室前前后后共留下過280多人伏案工作的身影。除了部分法學(xué)專家,其他多數(shù)是從政法大、北大、人大等法學(xué)院招聘而來做兼職的學(xué)生。他們?nèi)橥度耄瑥U寢忘食,有時因工作忘了時間,樓門鎖了,只得從二樓的窗口跳出來,有時索性就在書桌上一睡就是一晚上。現(xiàn)在在中國人民大學(xué)任教的金海軍老師,加入的時候還是人民大學(xué)的本科生,之后升入碩士、博士,留校任教,對詞典編纂工作卻一直不離不棄。回憶起過去的時日,他只用了一個詞來表達(dá)——“餐風(fēng)沐雨”。這里也時常回蕩著爭論的聲音。面對一個詞匯時各人都有自己的意見,由于大家對英美法都不夠熟悉,也很難制定一個統(tǒng)一的標(biāo)準(zhǔn)。在這種情形下,他們總結(jié)出一些“形而下”的標(biāo)準(zhǔn):一是要語出有據(jù),所做的詞條內(nèi)容和所發(fā)表的意見都必須是在地道的英美法中所表述的東西;二是尊重專業(yè),根據(jù)每個人的專業(yè)背景做分工,在有爭議不能協(xié)調(diào)時,也以該專業(yè)的人的意見的為準(zhǔn)。即使這樣,有的問題也仍然很難解決,比如有的詞條不僅涉及民商法內(nèi)容,還有關(guān)訴訟法,綜合性很強(qiáng),常常幾番爭論下來都難以有結(jié)果,也只有在日積月累中慢慢解決。我們現(xiàn)在所看到的詞典就是經(jīng)過不斷碰撞的結(jié)果,一個詞解釋的程度、高度就代表了團(tuán)隊(duì)對這個事物認(rèn)識的過程和高度。 還有一群德高望重的東吳老人,在薛波的情感中占據(jù)了最凝重的那一部分。東吳大學(xué)法學(xué)院于1915年成立于上海,是中國在教授中國法之外惟一系統(tǒng)地講授英美法的學(xué)院,解放前中國最著名的法學(xué)院之一。1952年,東吳大學(xué)被撤銷,英美法的研究長期停頓,英美法教育更是因此斷檔了幾十年。在薛波為找不到合適的審稿人之際,經(jīng)中國政法大學(xué)教授、本詞典的總審訂人潘漢典先生指點(diǎn),薛波前往上海,一家一家地叩開了這些曾在東吳大學(xué)法學(xué)院接受過系統(tǒng)英美法教育的老人的房門。然而老人晚年的境遇卻深深震撼了薛波。東吳大學(xué)被撤銷后,對東吳師生而言,與東吳法學(xué)院的關(guān)系成了一種罪過。在1957年“反右運(yùn)動”,以及“文革”期間,很多校友遭到迫害。后來雖得到平反,但至今許多老人晚景凄涼,多年都再未從事過與法律有關(guān)的事。被譽(yù)為“羅馬法活詞典”的周枏先生,晚年生活在破舊陰暗的木質(zhì)樓房中一間十余平米的小房間里,惟一值錢一點(diǎn)的家當(dāng)是一臺黑白電視,一個單開門冰箱。他年過九旬,雙手高度顫抖,只能委托80多歲的夫人來謄寫改正后的稿件。哈佛大學(xué)博士盧峻先生,是前中央大學(xué)法學(xué)院院長。在他的家里,惟一的電器是一臺巴掌大的電扇, 90多歲的他一目失明,戴著用舊信封糊住一邊的眼鏡來審閱稿件。辛勤地工作,卻幾番叮囑薛波不要署名,就連600元的微薄審稿費(fèi)也捐給了編輯部。 蔡晉先生,1930年代曾為浙江地方法院和上海特區(qū)法院法官,晚年與兒子、孫子孫媳三代共處一間小房中。重病纏身,在病床上親自審訂了49頁稿件。當(dāng)詞典的編撰工作接近尾聲時,終于溘然長逝。這樣的事例,在薛波來往京滬之間的30多趟里,充斥著他的眼目,也沸騰了他的血液,令他在困境里一次次振作前行。體弱多病的耄耋老人,為了被摧殘、埋沒得太久的生命能在逝去之前再美麗地綻放一次,為了能將自己的才學(xué)匯入蜿蜒流過的文化長河、不致磨滅,他們用自己虛弱的體力、堅(jiān)韌的毅力和強(qiáng)大的靈魂,為英美法詞典的完滿誕生作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(xiàn)。在薛波的一封信中,他如此寫道:“從道義上我們收入了太多本不當(dāng)屬于我們的摯愛,盡管它已化作一份份寄托溶入這套崎嶇的卷宗。” (三)“只有翻譯家掌握這種技術(shù),要領(lǐng)會外國語言真正的要義,要用本民族的語言表達(dá)出來,要表達(dá)得不失去本色。我們的工作也是這樣的過程,但比翻譯家更刻板,允許我們變化的空間更小,允許想象的程度更小。”——薛波 關(guān)于詞典編纂,薛波提得最多的一個詞是“摸索”。因?yàn)椴欢驗(yàn)闆]做過,也因?yàn)闆]有人做過。他們曾經(jīng)專程拜訪商務(wù)印書館、上海譯文出版社等大家公認(rèn)詞典做得比較好的出版機(jī)構(gòu),但聽到的總是“我們也在摸索”之類的話。我國對英美法的研究確實(shí)太過稀缺,薛波如同走進(jìn)一片荒蕪的曠野,材料缺乏,也探尋不到前人的足跡。“沒有前輩,沒有經(jīng)驗(yàn),一切都只能靠自己了!”最基本的工作是要確定參考藍(lán)本。但由于不了解英美法,就很難確定哪些文獻(xiàn)是最能代表英美法、在英美法國家最具權(quán)威的。摸索了至少三年,才明了美國的布萊克詞典在英美法系中的地位。 龐雜的詞目中,哪些是英美法的精髓,應(yīng)該重點(diǎn)予以闡釋?哪些意義不是那么重大,可以從簡帶過,甚至根本不需收入?沒有標(biāo)準(zhǔn),只能自己摸索。常常是一個詞洋洋灑灑、千言萬言,做了非常詳盡的解釋,到后來卻發(fā)現(xiàn)它其實(shí)并沒有那么重要,或者它的背后還有意義更重大的詞,于是又做刪減;有的詞原以為可以省略、從簡,慢慢又發(fā)現(xiàn)它其實(shí)有著深遠(yuǎn)的內(nèi)涵,于是重新補(bǔ)充。反反復(fù)復(fù),漸漸才成體系,人力、時間也都耗去不少。 編譯過程中,中國與西方法律文化的差異也突出的顯露出來。英美法系的法律制度與我國相去甚遠(yuǎn),有些制度在我國是沒有的,相應(yīng)的法律術(shù)語在漢語中根本找不到對應(yīng)詞,很難用合適、貼切的語言表達(dá)出來。薛波將英美法總結(jié)為“流動的、活躍的”,總是處于快速發(fā)展、變動中。而詞典又必須是確定的,越確定越便于讀者理解。此時他終于明白為什么一直以來沒有人去做這件事,或者做的也只是簡單的轉(zhuǎn)譯、對譯,就是因?yàn)檫@之間的鴻溝太難以跨越。難,并沒有讓他放棄。在不斷摸索中,他們掌握了一些巧妙的技術(shù),謂之“以靜制動”。在材料中找相對最確定的部分,丟棄相對活躍、對本身的含義不重要的部分。當(dāng)然,這個“找”的功夫,定然也是經(jīng)過了日日年年的錘煉。 詞目搜集、編譯完之后,還有編輯的問題。5萬多詞條,相當(dāng)于日本《英米法詞典》收錄的3倍,怎樣在合理的篇幅里以最系統(tǒng)、最協(xié)調(diào)、最經(jīng)濟(jì)的方式排列出來?薛波舉了一個例子來說明編輯工作的“細(xì)”——引見。我們經(jīng)常會在詞目的后面看見“見××頁××詞”的字樣,以表示對該詞的理解可以參見另外一個詞的解釋。這就是一個要把全篇的詞都統(tǒng)一綜合,再合理聯(lián)系起來的過程。然而,把這么厚的材料從頭至尾看一遍需要兩年,不說時間的有限,即使真的有人這么看了,等他兩年之后看到末尾,前面的也早已經(jīng)忘卻。分工負(fù)責(zé)是他們沒有辦法的辦法,每個人看一至兩萬個,這導(dǎo)致詞典的某一部分是統(tǒng)一的,但總體而言還不夠周全。對此,薛波寄望于讀者和社會的力量,“一輩輩不斷地進(jìn)行修訂、完善,也許若干年之后才能使我們的遺憾消除,達(dá)到恰如其分、完美無缺的境界。” 數(shù)不勝數(shù)的細(xì)節(jié)。每個細(xì)節(jié)都竭盡自己的努力和智慧去考慮、去鉆研,不斷的認(rèn)識,不斷的又有新的細(xì)節(jié)出現(xiàn),不斷的追求著完美。而與這種追求始終形影不離的,是物質(zhì)條件的極度窘迫。 “堅(jiān)持是一種非常難磨的心理,不知道什么叫終結(jié),不知道何時天亮,只有去忍受。”“不去追求可以,兩年完成也可以。但真的不想,不能割舍,然而自己的能力、時間又有限。很痛苦。”薛波將自己的痛苦歸結(jié)于他“對追逐細(xì)節(jié)的頑固”,但正是因?yàn)樗念B固,我們今天才可以說:《元照英美法詞典》不僅僅是一本詞典,它還確立了一種詞典編纂的制度!